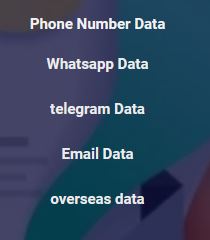小说对编织的,这一主题体现了西拉斯·马南在寓言和现实主义之间巧妙游走的方式。古典神话和童话故事中充满了织工。西拉斯像昆虫一样的活动(他被简化为“像一只纺线昆虫一样毫无顾忌的活动”,并且“似乎像蜘蛛一样,纯粹出于冲动,没有经过思考就编织”(第 14 页))让人想起阿拉克涅的神话,她大胆地向一位女神挑战编织比赛。在奥维德在《变形记》中给出的版本中,女神雅典娜承认阿拉克涅技艺高超,但愤怒地将她变成了一只蜘蛛。神话将阿拉克涅的编织描绘为巨大艺术力量的源泉,但其他故事也强调了编织的局限性:例如,在《侏儒怪》童话中,磨坊主的女儿因父亲的粗心大意而被囚禁并被迫将稻草纺成金子。在丁尼生 1832 年出版的《夏洛特夫人》中,这个“日夜编织”的神秘人物既暗示了创造力,也暗示了监禁。艾略特对这些故事非常感兴趣,以至于在 1873 年至 1876 年间创作了挽诗《艾琳娜》,讲述一位希腊女诗人,她在 19 岁时被母亲锁在纺车上,据说后来死去。在这里,织工也被判处“乏味地纺线 | 像昆虫一样劳作”;然而,与塞拉斯不同的是,“她眼中的激情 | 变成了悦耳的呼喊”。尽管编织是必需的,但埃琳娜还是形成了创造性的视野。
尽管编织给塞拉斯带来了一种麻木的职业而非创造性的视野,但这本小说仍然利用了编织和写作之间的诸多相似性,预示着《米德尔马契》中叙述者“在解开某些人类命运并看到它们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过程中要做很多事情”。文本一词的拉丁 台湾电报数据库 语词源textus让人想起“编织的东西、网、质地”(《牛津英语辞典》)。讲故事的语言充满了类似的联想,正如塞拉斯所表明的那样,他认识到灯笼场的弟兄们“策划了一个阴谋,将罪恶放在他的门口”(第 11 页),或者《彩虹》中的蹄铁匠“拿起话语的线索”(第 40 页)。叙述者对西拉斯“困惑的头脑中唯一能抓住的线索” (第 126 页) 的评论唤起了“线索”的双重含义:既是解决方案,也是“线团或毛线团”,就像阿里阿德涅带领忒修斯走出牛头怪迷宫时所用的线团或毛线团一样 ( 《牛津英语辞典》 )。讲故事和计算之间也有类似的暗示性联系。“讲”就是叙述,但也是列举或计算——例如,西拉斯“一直工作到深夜,才讲完奥斯古德夫人桌布的故事” (第 14 页)。西拉斯对钱币的非生产性、物质主义的“讲述”与艾略特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艾略特认为讲故事是一种向外看的模式,它揭示了社会网络般的本质,并产生了共鸣。《织工马南》对比喻和字面意思之间的错位很感兴趣;西拉斯失去了一堆硬币,但埃比却成为了更有价值的“新宝藏”(第 121 页)。正如玛丽·普维所探讨的那样,在这部作品中,“比喻胜过字面意思”,就像埃比与西拉斯建立的纽带使他比她“字面”父母戈弗雷更像她的父亲一样。
- Board index
- All times are UTC
- Delete cookies
- Contact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