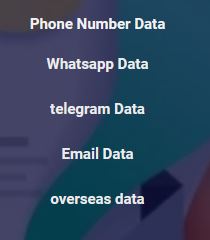工作组在分析这些问题时首先回顾了国际法院在德黑兰人质案([1980] ICJ Rep 1980 3 at [91])中强调的“错误地剥夺人类的自由并在艰苦条件下对他们施加身体限制本身显然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以及《世界人权宣言》所阐明的基本原则”。工作组接着说:
一国的管辖权和责任超越其领土边界,并提到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一贯判例。工作组和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此适用国际法院阐明的一般原则,并逐渐在区域人权法院(特别是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的判例中加以运用,尤其参见[以色列隔离墙 ([2003] ICJ Rep 136)]和[格鲁吉亚诉俄罗斯,临时措施 [2008] ICJ Rep 353 ]第[109]页,法院指出,“《消除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这些规定,与其他同类文书的规定一样,一般似乎适用于缔约国在其领土之外采取的行动”。人权条约的性质及其普遍性基础要求对其范围的领土限制予以正当化,这是人权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的结果(见[29])。
此外,工作组还表示:
这一一般规则的核心是,一国的国际法义务同样适用于其在 纳米比亚资源 国外的行为,也适用于其在国外代理人的行为,而且显然,当个人被拘留时,这一义务也适用。人权事务委员会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进行了“背景和目的性解释”,确认“缔约国必须尊重并确保在其权力或有效控制下的任何人享有《公约》规定的权利,即使这些人不在缔约国领土内”。[E/CN.4/2006/120,第 11 页] 人们普遍认为,被国家当局关押在国家领土以外的拘留设施中的人员受该国的有效控制(第 [31] 页)。
工作组得出结论,美国在拘留奥贝杜拉一事上受国际人权法的约束。在这方面,它还明确援引了国际法院的判例,该法院在迪亚洛案([2010] ICJ Rep 639,第 [77] 号)中指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9(1)-(2) 条原则上适用于任何形式的拘留,“无论其法律依据和目的是什么”。工作组强调,“将国际人道主义法应用于国际或非国际武装冲突并不排除人权法的适用。这两套法律是互补的,并不相互排斥”。读者可能会认为,尽管没有明确提及,但 WGAD 在此处又借鉴了国际法院的做法,即《核武器合法性》 [1996] ICJ Rep 226 [25] 和《以色列围墙》 [2004] ICJ Rep 136 [106]。总体而言,WGAD 明确依赖其他法院(尤其是国际法院)的判例,这一点令人震惊。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际法院已将其在世卫组织区域总部所说的内容变为现实,即国际法“并非在真空中运作”,而是“根据事实并在更广泛的法律规则框架的背景下运作,而国际法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980] ICJ Rep 73 at [10])。国际法院现在自由地引用其他法院和法庭的判例。这显然是一条双向的道路,而工作组在Obaidullah 案中巧妙地依赖国际法院的判例就是这种对话富有成效的一个例子(在这方面,还可参见欧洲人权法院院长 Spielmann 最近在国际法院就这一主题发表的恰当演讲)。
- Board index
- All times are UTC
- Delete cookies
- Contact us